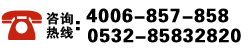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,书赠瞿秋白的条幅。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、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。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,可是,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。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,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、无私的帮助,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“最惬意的”时光。
同志相称
1931年1月,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,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。会后,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。此时,王明等正咄咄逼人,挑起党内斗争。这种无休止的功过是非的纠缠,让瞿秋白十分厌倦。他在《多余的话》中,毫不掩饰地庆幸自己“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”,终于又回到了“‘自己的家’——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”。
在上海,瞿秋白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。久别重逢,两人分外高兴,有说不完的话。瞿秋白高兴地对茅盾说:“雁冰,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,只是一直不得机会。现在好了,我也可以从事写作,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。”
还在离开苏区时,他就悄悄地向夫人杨之华透露了这样的心愿,即到上海后,一定要想方设法见到鲁迅。他恳切地对茅盾说:“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,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。唉,只是一直无以谋面,始终引为憾事。”茅盾和鲁迅很熟,常有往来,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,便对瞿秋白说:“秋白,你不用着急,只要有机会,我会引你去见鲁迅的。”
5月初,中央机关遭到破坏,瞿秋白来茅盾家避难。这天,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。于是,瞿秋白又与冯雪峰结识。他从左联刊物《前哨》上面读到鲁迅的文章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,读罢连连赞扬道:“写得好,到底是鲁迅。”他对冯雪峰说:“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,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,翻译一些俄国作品。雪峰同志,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?”
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,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澹如家住宿。谢澹如爱好文学,同情革命,其住所比较清静,居住十分安全。瞿秋白从此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。
一天,冯雪峰来到鲁迅家,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通报,鲁迅听后很振奋,他说:“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,他的《莫斯科通讯》,我看过,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。”他还告诉冯雪峰,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,将是一件好事。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,他早就想直接翻译俄文版本,并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项工作。他对冯雪峰说:“我们就抓住他!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!以他的俄文和中文,确是最适宜的了。”
这天,鲁迅和冯雪峰谈兴很浓,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,他说:“何苦(瞿秋白的笔名,作者注)杂文,明白畅晓,一览无余,真有才华,是真可佩服的。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!在国内文艺界,能够写这样论文的,现在还没有第二人。”
这年秋天,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《铁流》译稿。鲁迅检读译稿,发现序没有译,心中很是不踏实。《铁流》如果没有序,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。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,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。瞿秋白接受序文后,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,署名史铁儿。鲁迅读后十分满意,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:“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,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。”他还在《〈铁流〉编校后记》中赞赏道:
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,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,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。幸而,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,将近二万言,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。……
不久,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《被解放的董吉诃德》(今译堂吉诃德,作者注)剧本交由瞿秋白,瞿秋白用“易嘉”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,先在《北斗》刊载,后又出单行本,鲁迅则补译《作者传略》,并在《后记》中,称赞这篇译文:“注解详明,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。”他还说,在读过译本后,“那时我的高兴,真是所谓‘不可以言语形容’”。
鲁迅曾将日文版《毁灭》转译成中文,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。瞿秋白校读后,给鲁迅去了封长信,直接以“敬爱的同志”相称,说:“你译的《毁灭》出版,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……”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:
所有这些话,我都这样不客气的(地)说着,这自然是‘没有礼貌’。但是,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,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。这种感觉,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,和对自己说话一样,和自己商量一样。
鲁迅很高兴地读完这封长信,立即给瞿秋白回信,这封信以《论翻译》为题,发表在《十字街头》上。鲁迅的回信,开头以“敬爱的J?K同志”(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,作者注)相称,信中说:“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,使我非常高兴。”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,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。
风雨同舟
1932年初夏的一天,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,来到鲁迅家。他们的第一次会面,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,亲切自然,无拘无束,而毫无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矜持与尴尬。他们畅所欲言,从政治谈到文艺,从理论谈到实际,从希腊谈到莫斯科,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,也谈得津津有味,妙趣横生。
不知不觉间,已经到了中午,鲁迅特意准备酒菜,两人边饮边谈,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,直到夜幕降临,才依依告别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在女师大读书时,就曾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,此时她所看到的瞿秋白,比以前显得更老练、更成熟,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:
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,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,圆面孔,沉着稳重,表示出深思熟虑、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,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。
第一次见面后,瞿秋白热切期待着再与鲁迅的会面,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。可是,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,他们的行动十分不便。9月1日上午,天空下着绵绵细雨,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,以摆脱特务的盯梢,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,来到瞿秋白住处。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,很快便切入主题,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。瞿秋白对粤语陌生,特意找出几个字,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。
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,便悄然退出,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。可是,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,坐下用餐时,菜已经凉了,而且味道也不好,杨之华感到很不安,鲁迅却全不在意。席间,他和主人谈笑风生,十分亲热。
这以后,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,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,如“何凝”、“维宁”、“宁华”和“它兄”等。
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,写了短篇小说《豆腐阿姐》,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,可又有点害怕。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:“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。”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,亲切地称呼鲁迅为“大先生”。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,去打搅鲁迅的工作。瞿秋白则再三劝说道:“不要紧,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,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。”杨之华于是鼓起勇气,专程将文章送到鲁迅处。
鲁迅接过文稿后,便认真阅读,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,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,然后用纸包好送回。
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,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“围剿”,国统区内也弥漫着腥风血雨,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。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,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,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。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,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,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。
1932年12月23日深夜,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,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。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,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,“就向秋白同志说:‘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,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,免得我担心。’秋白同志答应了。一会儿,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,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:‘好走,不送了。’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,我回头望望,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,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,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。”
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,曾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:
雪意凄其心惘然,
江南旧梦已如烟。
天寒沽酒长安市,
犹折梅花伴醉眠。
这首诗写于1917年。那时,瞿秋白母亲自杀,家境破落,前景堪忧。他在失落、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,带着沉郁的“颓唐气息”。时隔15年,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,但是,他受排挤、打击,忍辱负重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。他将这首诗赠予鲁迅,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,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。
一次,当他用“犬耕”的笔名发表文章时,鲁迅不解地问道:“此寓意为何?”
瞿秋白说:“我不是政治动物,搞政治,无力量可济。耕田本是用牛的,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。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‘犬’。”
鲁迅听后微微颔首,稍顷,便又叮嘱道:“你对我说可以,不要再对别人说了,可能影响不好。”1933年3月,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,带来堇花一盒,以作乔迁之贺,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书写成条幅相赠。
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,坦诚畅怀地交换心迹,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并世奋斗的同志。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鲁迅的友情,以至在身陷囹圄、生死攸关之际,还时时思念这段他一生中“最惬意”的时光。
爱人以德
在上海养病期间,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生活,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,以他的政治身份,根本不可能谋得固定的职业,在当时的上海,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,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,惟能糊口而已,实难调养虚弱的病体。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,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,会有如此的惊诧和不安:
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,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。只见他满脸病容,面目浮肿,气色和神情都很坏。身上穿着一件长衫,破旧不合身,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。
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,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,以稿酬贴补困窘的生活。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,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书报刊的,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,以笔名发表文章。1932年11月4日,鲁迅在日记中写道:“晴,以《一天的工作》归良文公司出版,午后收版税二百四十,分与文尹六十。”《一天的工作》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,共收10篇小说,其中有杨之华初译、瞿秋白校定、以“文尹”笔名翻译的绥拉摩维支的《一天的工作》和《岔道夫》两篇。
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:
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,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:《坟场》、《莫尔多姑娘》、《笑话》、《不平常的故事》,想印一本书,换一点稿费。时值合众书局初创,需要买稿,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《二心集》的原稿拿去。书店只认得赢利的,不几天,先把《二心集》的稿费付了,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。
鲁迅知道后很生气,他告诉阿英,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,“否则他的《二心集》要拿走”。这样,“几经交涉,总算‘开恩’,抽买了一篇《不平常的故事》,把其余三篇退回”。稿酬也较高,“出千字3元”。
次年2月16日,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到上海,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,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。肖伯纳途经香港时,在发表的演讲中,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。于是,神经过敏的记者们,或褒或贬,毁誉不一,一时间,肖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。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,编成一本书,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。他们很快投入工作,先由许广平到四川北路的报摊上,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,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,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,署名乐雯,鲁迅作序,瞿秋白写卷头语,由野草书屋出版,书名为《肖伯纳在上海》。
鲁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,便有意帮助他,让他以卖文所得,来弥补经济生活的贫乏。《肖伯纳在上海》的出版,便是属于这种情况。
这年3月至10月,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。他抓紧时间,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:《王道诗话》(3月5日)、《伸冤》(3月7日)、《曲的解放》(3月9日)、《迎头经》(3月14日)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(3月22日)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(3月30日)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车》(3月)、《关于女人》(4月11日)、《真假董吉诃德》(4月11日)、《内外》(4月11日)、《透底》(4月11日)、《大观园的人才》(4月24日)、《儿时》(9月28日)、《中国文和中国人》(10月25日)等。
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说:
这些文章,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造的: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,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,经过两人交换意见,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,然后由他执笔写出。
……
鲁迅看后,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。
这些杂文,大多以鲁迅的笔名,在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等栏目发表。后来,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,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和《准风月谈》中。
瞿秋白在与鲁迅的交往中,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,一种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,并全面、准确地介绍、评价鲁迅。他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,排除所有干扰,专心致志地开始阅读和写作。白天,他躺在床上阅读鲁迅的作品;夜深人静时,便一人伏在一张小方桌上,不停地写着,一直写到天明。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,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:“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得多。”
瞿秋白的这篇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,长达1.7万字,第一次全面、正确地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,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。序言说:
鲁迅在最近15年来,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,尤其是杂感来得多。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,叫做“杂感专家”。“专”在“杂”里者,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。可是,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,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。
他在结束这篇序言时说:“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,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,我们应当向他学习,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。”《鲁迅杂感选集》由鲁迅交北新书局李小峰,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。
不久,瞿秋白又因为安全问题搬到鲁迅家避难。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脸,鲁迅心中泛起阵阵凄楚,他希望尽其所能帮助瞿秋白。在当天的日记中,鲁迅写道:“晴,热。午后大雷雨一阵。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,分付文尹、靖华各卅。以《选集》编辑费二百付凝冰。”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,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。这里的“《选集》编辑费二百”,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的编辑费,以帮助他们夫妇度过生活的难关。3年后,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,还说及此事:
我的选集,实系出于它兄(即瞿秋白,作者注)之手,序也是他作,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,弄出来卖几个钱的。
殊深轸念
1934年新年伊始,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。临行前,他向鲁迅辞行。这天晚上,他们彻夜长谈,一直到第二天晚上,瞿秋白才回家。瞿秋白满面笑容地告诉杨之华:“要见的都见到了,要说的话也说了。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,小海婴也很可爱。”
他是不太情愿离开鲁迅,离开上海,离开他所称之为“家”的文学艺术的阅读和写作的。在他的《多余的话》中,可以约略地揣摩出其难舍难分的心情:“1934年1月,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,又跑到瑞金——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——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。”
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。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:“像秋白那样的身体,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?如果他留在上海,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。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,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。”
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时,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,他致信曹靖华说:“它嫂平安,维它兄仆仆道途,不知身体如何耳。”“它”、“维它”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。
其实,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,而被留在江西,以孱弱的病体,与国民党军队周旋。1935年2月24日,瞿秋白被捕,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,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。在他给鲁迅的信中说:“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,分别多年没通消息,不知你的身体怎样,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,没有上学。二年前,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,病又发了,到福建上杭养病,被红军俘虏,问我做什么,我说并无擅长,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,对医学一知半解。以后,他们决定我做军医。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,你是知道我的,我并不是共产党员,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,有殷实的铺保,可以释放我。”信末署名“林其祥”。
显然,他在编造假履历,并将此告诉亲友,以诓骗敌人。接着,他又以“林其祥”的假名,给周建人去信说,天气冷了,狱中衣被单薄,很冷,需要一些衣服和钱,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,他是可以释放的。鲁迅读到这封信,心中尤为焦虑,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50元。
鲁迅的钱和杨之华改制的两条裤子,刚刚从邮局寄出,报纸便公开登载瞿秋白被捕的消息。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,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。鲁迅心急如焚,曾和陈望道相商,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,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现。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,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。鲁迅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将面临之结局,无比痛惜。5月17日,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:“那消息是万分的确了,真是可惜得很。”不多日,他又函告曹靖华:
它事极确,上月弟曾得确信,然何能为。这在文化上的损失,真是无可比喻。许君已南来,详情或当托其面谈。
这里的许君,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,时任蔡元培的秘书。鲁迅从他那里获悉,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,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,蔡元培提出在中国,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,应网开一面,不宜滥杀。但是,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。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,鲁迅深深悲痛,他在瞿秋白就义前7天,给曹靖华的信中说:“它兄的事,是已经结束了,此时还有何话可说。”
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,瞿秋白被害后,他在致萧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:
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,秋即其一。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,此外还很多。他有一本《高尔基短篇小说集》在生活书店出版,后来被禁止了。……中文俄文都好,像他那样的,我看中国现在少有。
他拿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比,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《死魂灵》。他告诉萧军:
《死魂灵》的原作,一定比译文好,就是德文译,也比中文译好,有些形容词之类,我还安排不好,只好略去,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,错误也较少。瞿要不死,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,即此一端,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。
瞿秋白就义后,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冷静的。他告诉曹靖华:“中国事实早在意中,热心人或杀或囚,早替他们收拾了,和宋明之末极像。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,只好仍是有一分力,尽一分力,不必一时特别愤激,事后又悠悠然。”
鲁迅从愤激中奋起,做实实在在的工作,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,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,印成两册精美的《海上述林》。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,“倘其生存,见之当亦高兴,而今竟已归土,哀哉”。
瞿秋白被捕后,鲁迅便与茅盾、郑振铎等相商,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。瞿秋白牺牲后,鲁迅也已是体弱多病、形销骨立了。但他硬是抱病忍痛,殚精竭虑,负责编辑、校对、成书的全过程。《海上述林》上册出版时,鲁迅对这本书十分满意,他说:“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,重磅纸;皮脊太‘古典的’一点,平装是天鹅绒面,殊漂亮也。”他还急于想看到《海上述林》下册。因此,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,“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,从速结束,我也算了却一事,比较的觉得轻松也”。鲁迅为《海上述林》所写的广告说:
作者系大作家,译者又是名手,信而且达,并世无两……足以益人,足以传世。
《海上述林》出版时,署名“诸夏怀霜社”,“诸夏”即是中国,“霜”为秋白的原名,“诸夏怀霜”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。“纸墨更寿于金石”,《海上述林》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,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,因为,它是“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,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”。